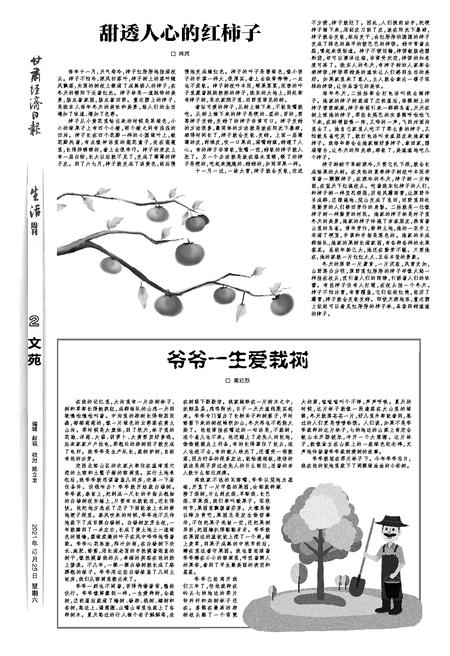□ 高红烈
在我的记忆里,大沟里有一片杂树林子,树和草都长得挺疯狂,成群结队的山鸡一天到晚嘎啦嘎啦叫着。中沟里的柳树长得特别茂盛,郁郁葱葱的,像一片绿色的云彩落在黄土山沟。那时候是大集体,到了秋天,林子里的花椒、洋葱、大蒜、胡萝卜、大黄要卖好多钱。后来家家户户拉电,那粗壮的柳树桩子就变成了电杆。我爷爷是生产队长,栽树护树,自然有他的功劳。
定西北部山区的农家大都住在崖湾里穴挖的土窑和土墼子箍的窑洞里。实行土地承包后,我爷爷就思谋着盖几间房,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没钱咋办?爷爷就开始栽白杨树。爷爷说,春首上,把剁成一尺长的手指头粗细的白杨树枝扦插上,只要有水就能活,还长得快。他把地方选在了庄子下面能放上水的耕地埂子根里。春风吹来的时候,爷爷迫不及待地栽下了成百棵白杨树。白杨树发芽生枝,一年就蹿到了一米左右,长成了黄土地上一道绿色的围墙,碧绿柔嫩的叶子在风中哗哗地唱着歌。爷爷心花怒放,挥汗如雨,在白杨树下改水、施肥、修剪,用长满老茧的手抚摸着笔直的树干,像抚摸着我的头,幸福的笑容在他的脸上荡漾。不几年,一棵一棵白杨树就长成了胳膊粗的椽子。爷爷用这些白杨椽盖了几间土坯房,我们从窑洞里搬出来了。
爷爷一刻也不闲着,苦得佝偻着背,隆然伏行。爷爷像郭橐驼一样,一生爱种树,会栽树,庄前屋后栽满了榆树、杨柳、桃树、椿树和杏树,路边上、塌窟圈、山嘴山湾里也栽上了各种树木。夏天路过的行人摘个杏子解解渴,坐在树荫下歇歇凉。我家掩映在一片树木之中,炊烟袅袅,鸡鸣狗吠,日子一天天滋润殷实起来。爷爷专门置办了长柄斧子和树剪子,平时修剪下来的树枝堆积如山,冬天再也不愁烧火柴了。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不栽树,连个雀儿也不来。他还瞄上了老先人的坟地,偷偷摸摸点上拧条,有的长得罩住了坟头,连人也进不去,有的被人砍光了,还遭受一顿数落,因为柠条的根系发达,能钻透棺板,迷信的说法是根子穿过老先人的什么部位,活着的亲人就什么部位疼痛。
离我家不远的瓦窑嘴,爷爷以荒地为基础,开垦了一片平整的果园,全部栽种嫁接了梨树,什么剥皮梨、早酥梨、长巴梨、苹果梨,我们都叫酸果子。深秋时节,果园里飘荡着芬芳。大概是物以稀为贵吧,果园总是发生偷窃事件,不但把果子洗劫一空,还把果树弄折,把园墙扒得豁豁牙牙。爷爷就在果园边的崖坎坎上挖了一个洞,铺上麦草,到果子成熟的中秋节前后,睡在里边看守果园。我也曾经跟着爷爷睡在小小的窑洞里,呼吸着醉人的果香,看到了平生最美丽的夜空和星星。
爷爷已经离开我们三年了,但他栽种在岭头七垧地边的那片针杵杆和杂树林子还在。喜鹊在最高的柳树枝头搭了一个背篼大的窝,喳喳喳叫个不停,声声呼唤。夏天的时候,这片林子就像一段遗落在大山里的绿锦,冬天就黑苍苍一片,好几里外都能看到,路过的人们更是啧啧称颂。人们说,如果不是爷爷栽种的这片林子,七垧地边的山梁上肯定会被山水开肠破肚,冲开一个大窟圈。这片林子,就像耸立在山梁上的一座绿色纪念碑,无声地传扬着爷爷栽树爱树的故事。
爷爷就埋在那片林子下。今年爷爷忌日,我在他的坟地里栽下了两棵绿油油的小松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