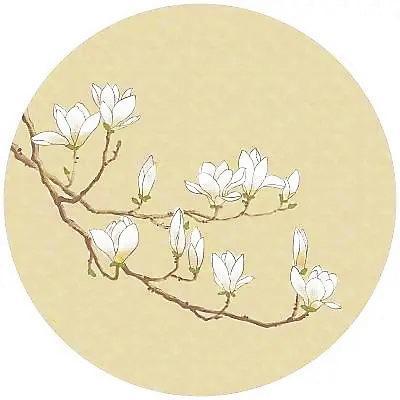文\张子艺
核心提示
天河注水,热辣滚烫;水自天河,笑凝东方。
这里是甘肃天水。
谈起天水的渊源 ,满满都是长辈故事里的盘古开天,崩裂山河;女娲补天,泥塑育人;羲皇合八卦阵列,分乾坤阴阳……而在甲辰龙年,天水却因着一碗热辣滚烫被大家熟知。就连没有去过天水的人,都在社交媒体上看着这些岩浆一般的辣椒汁流过碗,穿透手机,热烈地冲将了过来。
一 为了热辣滚烫的奔赴
一开始,当地人谁也没有把“麻辣烫”放在眼里,就像家里待客端上来一盘煮土豆,竟意外地获得了一致赞美。在一丝惶恐和不安中,天水人慎重而又骄傲地再端出来麦积山石窟、南北宅子、南郭寺;伏羲、女娲、羊皮鼓舞和社火;源源不断的呱呱、捞捞、然然、猪油盒子、丸子夹馍、浆水面……总之要把桌子放得满满当当,竭尽所能地捧出一场盛大的宴席。
从接受美食召唤的那一刻,因着麻辣烫而升腾起来的欲望就像一团火一样滚动起来。就像大地上掠起的风裹挟着风和雨,就像海平面上翻腾的浪一层层堆叠,那些红色的土豆,红色的豆皮,红色的丸子,红色的粉……到底有没有滤镜?
听说天水麻辣烫不用滤镜,所见即所得。
这显然引起了更大的兴趣——这到底是尖锐的辣还是敦厚的辣?听说还会麻,是不是要配着什么饮料喝?听说当地有一种奶茶,大杯还是小杯?要不要加糖?
就在这些碎碎念中,到底还是抵达了天水,伏羲画卦之地。
不知道是错觉还是真的,城里似乎飘着麻辣烫的香气,总之也是越走越近了。排了队,选了菜,老板在大锅里烫熟“刷刷刷”拌调料,一直到这会儿,才有了真实的触感,真来了?这就是麻辣烫?我在天水?!
一切幻觉在麻辣烫端在手里的时候得到了证实。从手机屏到现实,从长途跋涉到此刻安坐,那么就像一个美食博主一样充满爱意地开始这碗麻辣烫吧——再来一小瓶喝起来像橙汁但其实是胡萝卜素的饮料,据说这是甘肃小孩儿从小喝到大的,此刻权且当自己是个本地土著一样吃麻辣烫吧。
果然是红色的土豆,红色的豆皮,红色的丸子,红色的粉,确实没有滤镜,据说这种艳丽而不辣的辣椒来自本地,也就极大程度地解释了此次“天水麻辣烫”的猛烈出圈。
麻辣烫总归是辣的体验,吃粉的时候,要是有个猪油盒子,不知道有多妥帖。
虽然在当下时髦的食物搭配中,“淀粉”配“淀粉”简直是肥胖之源,但在西北的很多地方,这种经典搭配不要太多哦。陕西的大饼夹凉皮,甘肃的土豆馅儿饺子,最近流行起来的土豆泥拌面,都是这种逻辑的集大成者。
况且,一碗手擀粉里,如果啃上一个底和边烤得脆脆的猪油盒子,手擀粉麻辣鲜香的料汁可以为猪油盒子的味道锦上添花,同时脆的口感又能与充满韧性的手擀粉相得益彰,珠联璧合。
二 开启天水人的早餐
其实,猪油盒子的“CP”是呱呱。
这是天水人最难忘的朱砂痣,是出走半生依旧眷恋的故乡美味,是每个游子试图真空打包,带到全国各地的“呱呱”。
西北彪悍,讲话掷地有声,每个词的发音都硬邦邦的。但在天水,确实有很多可爱的“叠词”。“呱呱”“然然”“捞捞”,这些词的可爱程度,大概只有四川话才能媲美了吧,“拿个凳凳儿”“花生壳壳儿”,硬汉都能变成绕指柔。
对于这个名字,我曾和天水籍的同事展开过深入讨论,她家里有一个“呱呱摊摊”,在制作手艺上,她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每一个步骤,我甚至不用怀疑,要是拥有一些荞面,我都能做出“呱呱”来。
她说,呱呱是一个动作,因为荞面装在盆子里蒸熟,装到碗里需要拿着勺子刮下来,久而久之这个食物的名字就变成了“呱呱”。虽然说起来确实有道理,但这个解释我并未询问过更加权威的人士,姑且当作一种角度吧。
对于如今一切食物精细化的制作来说,“呱呱”显然是粗粝的一种地方美食,信手捏成的块儿可大可小,可粗可细,一点没有给当前饮食的“标准化”给面子。浇好调料的呱呱,还可以由食用者自己拿筷子夹成更碎的碎末,这样才能更好地拌匀调料。
参与感显然也是吃“呱呱”很重要的一个仪式感。
无论是现烫的麻辣烫,还是呱呱,抑或等一下要说到的凉粉浆水面,都是一种唯有在这种作坊里,才保留着亲手擀的面条,擀的粉,现场捏的呱呱和切凉粉。
从制作者的手中到食用者的眼前,这个过程不超过60秒,炒好的菜还带着锅气,凉粉上还带着漏网的棱角,浆水面上撒的香菜还支棱着筋骨。
“呱呱”需要在一片赤红色的辣中翻翻捡捡,寻寻觅觅,寻到一块儿裹满辣椒且大小适中的碎块,香气就这么吃到肚子里了。
“然然”和“捞捞”跟“呱呱”是同宗的食物。
都是杂粮蒸煮制作而成,“然然”和“捞捞”更加充满韧性,浸泡在调料里的食物需要筷子强行地切割成块儿,才能入口。但这两种食物无意间切中了如今一种“糯叽叽”的网红口感,这次在前来天水游客的反馈中,也证明了这种观点。
三 乡愁就是一碗浆水面的味道
很多人试图归纳浆水的味道。
他们类比的是北京的豆汁儿,我明确表示不对。
豆汁儿是经过猛烈发酵后的最终形态,但浆水只是略微地发酵出一点点酸气,就不由分说地被煮熟,那些益生菌也好,细菌也好,早都在煮沸中停止了发酵,浆水始终是一种“微酸”的口感,那种极酸的浆水是要被倒掉的,发酵过头了。
浆水的酸,至多跟广西的酸粉、酸浆是同类型。
这种酸跟醋的酸显然也不一样,浆水是一种植物性的酸,带着草木清新冷冽的气息;醋是浓缩而尖锐的酸,甚至醋的颜色都格外浓重起来。
用了这么多描摹的手段,其实也很难说清楚一种食物的味道。
既然到了天水,那么就去尝一尝天水的浆水面吧。
迎面而来的是香气,一种奇异而山野的香气。这种被称为“韭菜花”的野菜,也只有在浓烈的油脂中才能迸发出毕生最浓烈的香。
我曾经尝试用葱花、蒜苗儿、韭菜等调味蔬菜,模拟出韭菜花的香气,但这些实验均告失败,只有那些在大地间生长,沐浴过阳光和风雨的野生韭菜花,尖锐的香气才能扑面而来,带着山野的气息。
浆水面大多是手擀面条,也可以揪成面片,不过揪面片算是一个更加家常的隐藏菜单。我的天水同事在浆水面店里不遗余力地用方言大套近乎,店家才趁着人少勉为其难地为我们揪了两碗面片子。
手擀面跟手擀粉一样,如今已经是一种稀缺的做法了,压面机可以压出一切形状的面条儿。但从小吃手擀面的味蕾能感觉到其间微妙的区别,或许是冷硬的态度,或许是格外完美的形状,总之,他们尝上几口,就能发现端倪。
这是从小被父母的手擀面驯化的孩子。说到底,手工食物,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链接。
吃浆水面,最好配丸子夹馍。
这原本是天水的早餐,但油炸过的土豆丸子实在过于风靡,所以也顺理成章成为烧烤摊、麻辣烫摊上的常客。
烤热的白饼,烤热的土豆丸子。
据说白饼是馕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原时的变种,不知道,甘肃人从小吃着这种跟脸差不多大的饼长大,夹烤肉夹辣子夹丸子夹一切。
天水的烤饼自然要刷足够多的甘谷辣子,烤饼很快被辣到通红,烤好的丸子、蔬菜抽出钎子。还没完——虽然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但如果停在此处,显然就不是一个完美的丸子夹馍了。
还需要制作者拿起她的刷子——蘸满调料的刷子在夹好菜的饼里面刷大量的调料,依稀有黄绿色的孜然、小茴香,还有更大量的红色的辣子,再撒一些芝麻之类的“添头”,这才呈给满心欢喜的孩子们。
四 共享天水的夜色和晚风
捧着丸子夹馍逛逛天水吧。
伏羲女娲大地湾。
最近有一个段子很火:“别的城市火起来的都是古风,天水火起来的是上古风。”
伏羲手里抱着太极图,女娲手里抱着娃娃;《天水千古秀》的演员们穿着草皮兽皮裙在天水古城里热舞;大地湾的彩陶“小祖宗”站着迎客,这个名字实在令人费解到不敢深想。
但甘肃的审美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主打真实,这个娃娃脱胎于来自大地湾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确实已经有5100多岁了。
此地是秦人发祥地。秦人先祖自东方而来之后,在这里草原的边边角角里,艰难地生存。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几百年间,这个家族缓慢而不停歇地往中原挪动着,张家川、礼县、关中地区,最终称霸中原。
麦积山。
“麦积八景”虽然分布在各个季节,但至少当下的麦积山是要去的。小沙弥在佛龛里永久地微笑着,历史的烟云始终都笼罩在麦积山上,影影绰绰。
栈道拾级而上,北魏、隋唐、宋代佛造像拈花含笑。
当年工匠们叮叮咚咚的声音已经消逝在历史的风烟中了,但当前工匠们制作的文创产品,被捏在手里,被挂在包上,被作为礼物,带给各地的朋友。
麦积山有文创雪糕,有非遗传承人指尖的绣品,有文创毛绒玩具,尤其有一个掌心大小的微缩版麦积山,呆头呆脑又形神兼备,这是带得走的天水。
自由路的玉兰花开得铺天盖地,整条街都被这种盛大而隆重的春天覆盖,接着是杏花、桃花、苹果花、樱桃花。接着开始挂果子,整个春天的希望都被这些丰饶的果实实现,天水的大樱桃,不知道有多么美。
但是此刻,在天水,在天水的夜色之下,就让我们共享这个春天的暖风和水汽吧,毕竟明天,又是一个新的烟火征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