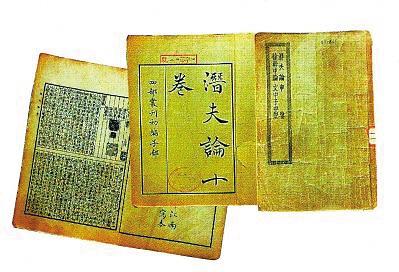本报特约撰稿人 马世年
王符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与王充、仲长统并称“后汉三贤”或“东汉三杰”,韩愈曾作《后汉三贤赞》,称赞其人,钦慕有加。其《潜夫论》是东汉最重要的子书之一,也是两汉子书的代表性著作。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说:“符书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刘熙载《艺概·文概》也说:“《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将其与董仲舒相提并论。这些评价,王符当之无愧!
王符的生平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后汉书·王符列传》(以下简称“本传”)记载说:“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著其五篇云尔。”以下又说:“后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乡人有以货得雁门太守者,亦去职还家,书刺谒规。规卧不迎,既入而问:‘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顷,又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符竟不仕,终于家。”
王符的生卒年代,学者们是讨论得比较多的。不过,因为本传记述的简略,只能是根据相关材料来推论。总体来看,所依据的材料,一是本传所说的“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一是皇甫规解官归安定的时间。这些都可以根据《后汉书》来确定:
马融“于延熹九年卒于家,年八十八”(《马融列传》),则其生卒年为章帝建初四年到桓帝延熹九年,即公元79-166年;
张衡“于永和四年卒,年六十二”,则其生卒年为章帝建初三年到顺帝永和四年(《张衡列传》),即公元78-139年;
崔瑗“于汉安二年病卒,年六十六”(《崔骃列传》附崔瑗传),则其生卒年当为章帝建初三年到顺帝汉安二年,即公元78-143年;
窦章“于建康元年(144年)卒于家”(《窦融列传》附窦章传),其生年不可知,但应该与马融、张衡、崔瑗等相若;
皇甫规生于和帝永元十年,卒于灵帝熹平三年,即公元104-174年(《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享年71岁。而其解官归里应在桓帝延熹六年(163)三月以后(《后汉书·孝桓帝纪》)。
可以看出,马融、张衡、崔瑗等人几乎同年出生,都在公元78、79年,窦章也应该在此前后。本传特别强调王符“少好学”且“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根据文意,其生年应与这几人相若。我们将其定为公元80年左右。皇甫规解官归里在公元163年后,他归安定后王符曾去拜访,那么王符卒年至少应该在本年以后,考虑到此时他也年事已高,我们将其卒年断在公元165年前后,其年寿在85岁上下。看来,王符诣皇甫规时,已八十余岁,故皇甫规一见面即予以携扶,“援手而还”,以示尊重与照顾。
关于王符名、字的含义,传统都采用《说文解字》的说法:“符,信也。”符信是古时的信物,用作通行的凭证,有符有节,也叫符或信。符节、符信意思都是关联的。“符”与“节信”正好是相互对应、互为解释。
《潜夫论》的分卷与题意
《潜夫论》共10卷,33篇。卷一包括《赞学》《务本》《遏利》《论荣》《贤难》五篇,其主旨是总论治国与论士,“赞学”则为全书之开篇,因而在体例安排上有着特别的用意。
卷二包括《明暗》《考绩》《思贤》《本政》《潜叹》五篇,主要谈君道与用人,集中体现出王符思贤、用贤的人才思想,也贯穿着“贤难”之愤,思贤、用贤,乃至嗟贤、伤贤也成为《潜夫论》一个重要而突出的主题。
卷三包括《忠贵》《浮侈》《慎微》《实贡》四篇,主要论臣道与时弊,尤其是当时的弊政。
卷四包括《班禄》《述赦》《三式》《爱日》四篇,核心是论议政事,尤其侧重具体政令,其所针对的依然是汉末的衰政。
卷五包括《断讼》《衰制》《劝将》《救边》《边议》《实边》六篇,承上论政的主题,更加侧重治讼和治边,其中“治边三论”尤为重要。
卷六凡《卜列》《巫列》《相列》三篇,专论卜筮、巫史、相人诸事。列,即“论”,《卜列》《巫列》《相列》与下卷《梦列》,分别探讨求神问卜、相人占梦等鬼神祭祀、世俗迷信之事,在《墨子·明鬼》《周礼·春官·占梦》《灵枢经·淫邪发梦》以及《论衡》的《骨相》《订鬼》《卜筮》《诘术》等专论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所做的集中论述,可称之为“潜夫四列”。
卷七除《梦列》外,还有《释难》一篇,《释难》即解答诘难,文章假托庚子、伯叔、秦子等与潜夫辩难,以申说作者的主张。
卷八包括《交际》《明忠》《本训》《德化》《五德志》,内容颇为总杂,《交际》论人际交往,《明忠》论君臣之道,《本训》论宇宙本源,《德化》论道德教化,《五德志》论帝王世系,各有所重,很难以统一的主题来涵盖。这当是作者在编排、整理全书时,将一些主题相对分散、不好集中或前面未列入的文章归在了一起,近似于“其他”一类。这一类还应当包括上卷的《释难》。而其中《本训》《德化》两篇,更多哲理思考,已带有哲学总结的意味。
卷九单列《志氏姓》一篇,论述姓氏源流,文末云:“略观世记,采经书,依国土,及有明文,以赞贤圣之后,班族类之祖,言氏姓之出,序此假意二篇,以贻后贤参(原作今)之焉也。”可见其著作之意。此外,王符在衰汉季世作《五德志》与《志氏姓》,叙帝王谱系、姓氏源流以见古史之兴亡,其背后的用意颇值得仔细玩味。
卷十《叙录》为全书总序,阐明著述宗旨。先秦两汉著述,多以书序置后,或综论学术大端以为总结,或说明撰述意图与写作目的,《庄子·天下》《荀子·大略》《韩非子·显学》以及后来的《淮南子·要略》《史记·太史公自序》《法言·法言序》《汉书·叙传》等,都是每书的书序(《荀子·大略》与《韩非子·显学》以下还有几篇文章,当是门下弟子及后学的附入)。一直到南朝刘勰著《文心雕龙》,还是这样,以《序志》为最后一篇。本篇逐一总结全书各篇题旨,说明著述目的,作为全书的总括。
《潜夫论》的题名,也有特别的意思。刘文英先生在《王符评传》中说:“‘潜夫论’者,‘潜夫’之论。‘潜夫’为作者自谓……‘潜夫’首先表明作者是一位隐居山野、身在下位的‘处士’,同时还表现了作者对于自我价值的一种认识和对世俗、时代的一种抗议。这种说法是很深刻的。”本传所说“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有些研究者批评其“肤浅”与“不当”。其实,范晔所说的“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只是谓该书以“潜夫”的自号为书名,而不是著其姓名,使之显之于众。之所以“不欲章显”,既和王符的隐居有关,也和他“耿介不同于俗”,“不得升进”的经历有关,因此才以“潜夫”之名,“讥当时失得”“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这就和前面所说的“志意蕴愤”“隐居著书”一致起来了。
《潜夫论》的思想主旨
《潜夫论》的根本主张与基本命题,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概括,这就是:重学务本,重德尚贤,重法明刑,重民救边。
重学务本是《潜夫论》的立论之基。全书以《赞学》为第一篇,继承了先秦诸子“劝学”的传统,以学为先、勉人向学。王符以学为“智明所成,德义所建”(《叙录》),认为“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赞学》),勉励为学的意图非常明显。可以说,重学的思想始终贯穿全书,从而成为全书的纲领。《赞学》之后,紧跟着便是《务本》,正可见作者也是将其作为全书的基础问题。王符主张崇本抑末、守本离末,强调富民正学,以之为治国之本。举凡贡士、举贤、考绩、班禄、论荣、交际、劝将、治边等,都要务本抑末,“慎本略末犹可也,舍本务末则恶矣”。他还提出,“务本则虽虚伪之人皆归本,居末则虽笃敬之人皆就末”——这已超越了道德品格的限制而深入到人性的层面了。
重德尚贤是《潜夫论》的根本主张。王符是儒家学说忠实的尊崇者和倡导者,也是东汉儒家思想的标志性人物,他注重德治、强调举贤,尊崇德行道义、主张选贤任能,以之为国家治理的理想方式。在王符看来,“仁重而势轻,位蔑而义荣”(《论荣》),因而提出“德化”的主张,以之为国家治理中最基本也最理想的方式,这也是儒家一贯的主张。尚贤也是《潜夫论》的核心思想,全书无不关涉到尚贤、任贤的问题。王符坚持“国以贤兴”,主张“任人唯贤”,一再强调尚贤、任贤、举贤、知贤;反对“任人唯亲”,猛烈抨击“以族举德”“以位命贤”的用人方式。
重法明刑是王符论政的鲜明标志,也是他思想中独具个性的方面。王符作为东汉时期儒家的标志性人物,在服膺德治思想的同时,能够正视商、韩之说,融合儒法,重法明刑,这是超越时代的进步之论。他吸收了商、韩等法家思想,将其融入自己思想体系中,从而成其一家之言。这较之于以往的儒家思想,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飞跃。王符认为,法令是君主统治天下最重要的手段,君主必须要做到令行禁止,否则就会危及国家。他面对汉末的衰世,深刻认识到,德治不能离开法制,仅仅依靠道德教化是不够的,必须要“兼秉威德”“明罚敕法”,德法并举;严刑峻法,“以诛止杀,以刑御残”。王符论法,多将其与赏罚结合起来,主张信赏必罚、厚赏重罚:“其行赏罚者也,必使足惊心破胆,民乃易视。”(《明忠》)这也是他在衰乱之世的无奈之法。
重民救边则是王符论政的基本立场。他继承了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并将其进一步发扬,提出了“民为国基”(《叙录》)的主张。他说“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救边》),“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爱日》)。因此,君主只有重民、爱民、利民、养民,关心民生疾苦,才能保其社稷、安其天下。这也是《潜夫论》中最具思想光芒和人文关怀的方面。由此,王符对于边地问题也予以热切关注。在如何处理边患的问题上,朝廷有各种杂乱的声音,包括“弃边”这样的浅薄之论。王符对此问题的认识相当深刻,他激烈抨击地方长官软弱无能、节节败退、欺瞒朝廷、残害百姓的罪恶,坚决主张“救边”“实边”,“边无患,中国乃得安宁”(《边议》);而“弃边”只能带来“唇亡齿寒,体伤心痛”的结果。如此集中地讨论“救边”问题,这在汉代子书中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