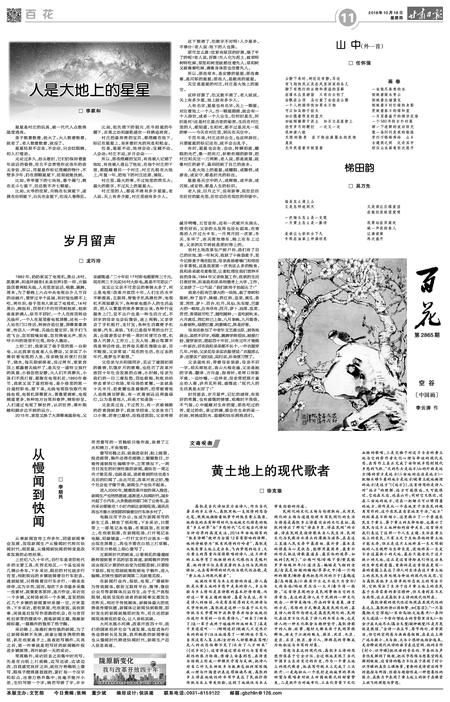□ 龙巧玲
1982年,奶奶家买了电视机,黑白,8吋,凯歌牌。和连环画册《未来世界》里一样,方脑袋顶着两根天线,人在里面说话、唱歌、跳舞。周末,为了看晚上六点中央电视台少儿节目的动画片,要穿过半个县城,有时饭也顾不上吃。两年后,巷子里有人家买了电视机,14吋黑白。晚饭后,四邻们不约而同到他家,他家夜夜挤满人。信号不好时,一个人在房顶转动天线杆,一个人在屋里看电视屏幕,还有一个人站在门口传话。转到合适位置,屏幕图像清晰,传话人一声喊,天线位置定好。孩子们飞进飞出,忽而鼓噪如雀,忽而鸦雀无声,那大呼小叫的场面不壮观,却令人激动。
上初二时,我家买了巷子里的第一台彩电。从此我家也夜夜人头攒动,父亲买了小凳供看电视的人坐,母亲晚饭后便打扫屋子,烧水,每天陪到深夜。没过两年,家家房顶上都矗着天线杆了,是天空一道特立独行的风景。小巷忽然安静,大人们不再聊天,小孩们不再打闹,都聚在电视机前。1990年春节,我家又买了遥控彩电,是小巷里的第一台遥控彩电。接下来,无线电视很快取代有线电视,电视机屏幕更大,图像更清晰,电视频道更多,各种地方台雨后春笋,精彩纷呈。人们通过电视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填补眼睛和脚步达不到的远方。
2015年,家里又换了大屏幕液晶彩电。父亲感慨道:“二十年前17吋彩电都要两三千元,现在两三千元买55吋大彩电。真是不可思议!”
其实让父亲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何止是电视!改革开放四十年,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互联网、智能手机风靡世界,电视机不再独霸天下。各种家电提升人的生活品质,把人从繁重的家务解放出来。各种行业服务上门,足不出户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不识字的母亲也会玩微信,迷上网购。父亲学会了手机银行、支付宝,各种生活缴费手机就够。汽车、高铁、飞机已是很平常的出行工具,出国游签证护照一周时间便可办理。机器人代替人工劳力,上天入地、腾云驾雾不再是神话传说。世界每天都在推陈出新,目不暇接。父亲常说:“现在的生活,在过去的年代,做梦也不敢想。”
父母亲与共和国同岁,见证了建国初期的激情,饥饿岁月的磨难,也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社会发展的点滴。小时候,母亲为我们的一日三餐发愁,四处借粮,秋收后结伴去青羊口农场、军马场拾麦穗,一去就是十天半月。拾麦穗也是偷偷的,经常被看地人追得满田野跑。有一次看到远远两盏绿灯,以为是看地人,后来才知是狼……
父亲卖过血,干过苦力。有一次被铺路的沥青浇到脖子。我放学回来,父亲坐在门口小凳,沥青已凝结。没钱进医院,父亲疼得龇牙咧嘴,五官变形。还有一次被开水浇头,烫伤好后,父亲的头发再也没长起来。在青海给人开过大卡车,一月两月回一次家。冬天,车坏了,冰天雪地修车,晚上在车上过夜,父亲的关节病就是那时得上的。
农村土地改革包产到户后,我们有了自己的田地。第一年秋天,收获了十麻袋麦子。至今记得麦子堆在院里,母亲高扬着嗓门和邻居分享喜悦。这是我家第一次有这么多的粮食。我和弟弟滚在麦堆里,让麦粒埋住我们营养不良的身体。1984年父亲恢复工作,我家的生活日渐好转。后来我和弟弟相继考上大学、工作,父亲舒了一口气说:“我们家终于抬起头了!”
我家小院有巴掌大的一块地,栽了枣树和梨树,种了茄子、辣椒、西红柿、韭菜、黄瓜、香菜、苦苣、萝卜、百合、牡丹、凤仙、矢车菊。巴掌大的一畦地,应有尽有。四月,萝卜、油菜、韭菜、苦苣、香菜就可吃了,随吃随种,一直吃到秋末。六月黄瓜、西红柿已上架,八月枣熟,九月梨香。从春到秋,绿肥红瘦、姹紫嫣红,煞是好看。
母亲还参加了中老年文艺演出队,到各地演出。虽然不识字,唱歌、跳舞学得很快。她爱打扮,爱穿新衣。想起四十年前,只有过年才能做一件新衣,好在我和弟弟都不长个,一件衣服穿几年。开始,父亲见母亲买衣服便说:“衣服那么多,还要买?”说归说,买归买,后来便习惯了。
父亲退休后,带着母亲旅游。母亲不识一字,却天南地北,高山大海走遍,父亲是她的字典、翻译、方向盘、指南针。老两口形影不离,一边吵嚷,一边伴老。母亲常把照片拿出给人看,讲所见所闻,感慨说:“现代人的生活真是太好了!”
时间逝去,岁月留声,记忆的滤网,有美好的希冀,也有感慨的情愫。艰难时不畏惧,不气馁,心中蕴藏对生命的爱,那些吃过的苦,受过的伤,承过的痛,都会在生命的某一时刻,转换成阳光、温暖和快乐拥抱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