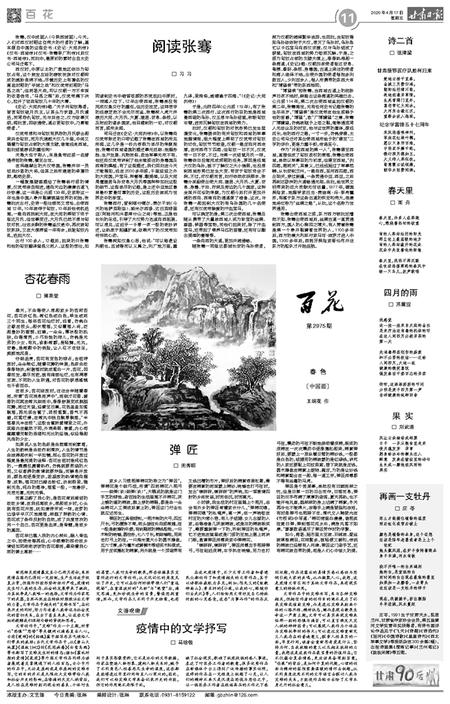习习
张骞,汉中成固人(今陕西城固)。今天,人们对西汉时期这位伟大的行者的了解,基本源自中国的这些史书:《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后汉书·西域传》。而此中,最原初的素材出自太史公司马迁笔下。
西汉时,中原以北的广袤地区依旧为匈奴占有,这个披发左衽的游牧民族对汉朝构成的威胁连绵不绝。尽管历史上有著名的汉高祖时期的“平城之战”和汉武帝初期的“马邑之战”,但两场大战,均以汉朝一方不体面的收场告终。“马邑之围”后,汉武帝痛下决心,拉开了征战匈奴几十年的大幕。
《史记·大宛列传》载:“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吉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
汉武帝想和与匈奴有夙怨的月氏联合起来共击匈奴,而月氏遥距大汉几千里,中间又隔着为匈奴占领的大漠戈壁,谁能远赴西域,担此结盟游说的重任呢?
天降大任于斯人,本是皇帝近前一名普通侍郎的张骞,横空出世。
在英雄辈出的大汉帝国,张骞并非一员征战沙场的大将,但其之后所建造的卓著功勋,彪炳史册。
一幅敦煌壁画描绘了张骞临行前的情景,汉武帝亲自相送,通向天边的漫漫古道飞沙弥漫。这一年是公元前138年,史家称这一年也是中国人睁开眼睛眺望世界的初始。张骞此次出行,史诗一般壮丽而又悲怆。出使西域12年,10年被俘于匈奴。10年后他伺机逃离,一路向西找到大宛,在大宛的帮助下终于抵达月氏。但世事变迁,大月氏已然不想与匈奴对抗。壮志未酬的张骞返汉途中,再次被匈奴抓获,又在大漠滞留一年有余,后趁匈奴内乱,逃回大汉。
出行100多人,12载后,回来的只张骞和他的匈奴翻译堂邑父两人。这般的悲壮,如同读到史书中皓首苍颜的苏武回归中原时,一样感人泣下。12年出使西域,张骞虽没有完成汉皇交付的重任,但历史注定,这样悲辛的远游定然不会无功而返。张骞深入虎穴并游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安息、条枝,以及附近的诸多国家,他目睹到的一切,对汉朝而言,前所未闻。
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以张骞向汉武帝陈述的口吻记载了张骞在西域的所见所闻。这几乎是一份内容极为详尽的考察报告。张骞对西域诸国的描述事无巨细:地理形胜、生产发展、风物民俗、政治军事无所不有。他还向汉武帝讲到了他未能前往的身毒国及西南的滇越。有了这些描述,我们因此在今天才能得知,远在2000多年前,千里迢迢之外的大宛国,产宝马、种葡萄、酿美酒,以及大宛周遭康居乌孙安息大月氏等国种种如此这般的细节。这些详尽的记载,是上述中亚地区最早最朴素最可靠的历史,这段历史被视为世界史中的珍宝。
张骞西行,曾到喀什噶尔、费尔干纳(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帕米尔西缘、达巴克特里亚(阿姆河和兴都库什山之间)等地。正是他长长的足迹,引导了大汉势力迅速向西拓展。可以想见,这近乎一千零一夜一般的奇妙讲述,让热衷于拓疆扩域,欲御天下的汉武帝如何怦然心动。
张骞深知汉皇心思,他说:“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史记·大宛列传》)
于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有了张骞的第二次西行。这次西行的目的地是西域最西端的乌孙。汉王想与乌孙结盟,砍断匈奴右臂,进而瓦解匈奴在西域的势力。
此时,汉朝和匈奴的对抗形势已发生显著变化,张骞提供的有关匈奴和西域的军事地理情报,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汉武帝对匈奴的讨伐,匈奴节节败退,汉朝一路压向河西走廊,在河西布下四郡。但匈奴一日不灭,汉武帝一日不安。不过,与第一次结盟月氏一样,张骞依旧没能完成预期的任务,原因是远离大汉的乌孙,既不了解汉之大小强弱,也没想到西域形势已发生大变、苟安于匈奴终会不测。不过,对汉朝而言,此行依然收获颇丰。张骞分派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田、扜罙及旁边的几个国家,这种全面开花似的考察,为汉朝今后打开更加开阔的西向、西南向的通道做了准备。这次,与张骞一起回到大汉的有乌孙国的几十名使者,还有汉武帝挚爱的汗血宝马,
可以确定的是,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及随从携带了大量被西域人视为珍宝的丝绸、漆器、铁器等宝物,而他们回来时,除了汗血宝马,还带回了喂养马匹的苜蓿,还有可以酿出美酒的葡萄等。
一条向西的大道,更加开阔通畅。
随张骞一同抵达都城长安的乌孙使者,深为汉朝的阔绰繁华诧异。也因此,当匈奴得知乌孙欲依附于大汉,想灭了乌孙时,乌孙急忙以千匹宝马向西汉求援。汉与乌孙结成了联盟,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彻底瓦解。于是,之前为匈奴占领的戈壁大漠上,渐渐热闹起一条商道。《史记》载:汉朝加派使者抵达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古道上来往的使者和商人络绎不绝,出使外国的使者每批多则数百人,少则百余人,每人所携带的东西大体和“博望侯”带的东西相同。
“博望侯”即张骞。当西域古道上的驼铃声日夜不绝时,踩踏出这条商道的英雄已去。公元前114年,第二次出使西域返回汉朝的第二年,张骞离世,无有任何史书记载张骞的生卒年岁。“博望侯”是汉武帝在他生前赐予他的官爵,“博望”,取“广博瞻望”之意。张骞广博瞻望,仿佛被赋予上苍之眼,能够通览常人无法企及的时空,他与这世界的惠泽,源远流长。他的西行之路,一寸一步,仿佛穿凿。太史公司马迁对其出使西域所给予的“凿空”二字的评价,更是力重千钧,传诵至今。
作为“开拓西域的第一人”,张骞凿空西域,直接促成了匈奴政权的衰落。张骞出使西域,虽然以军事目的为初衷,但凿空西域,“列四郡,据两关”,其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军事范畴。从长安到兰州,一路向西,至河西四郡,西出阳关,穿过新疆,一条贯通中亚、西亚,之后再到达欧洲的大道畅通无阻。由此,给世界文明带来的巨大贡献无可估量。1877年,德国探险家、地理学家巴龙·费迪南·冯·李希藿芬,有感于东方这条古道的恢宏和伟大,浪漫地将它称为“丝绸之路”,从此,这个名称为世界通用。
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东方西方彼此还懵然不知。张骞出使西域后,丝绸古道一直贯通到西方,国人的心胸因之博大。有人赞誉张骞是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1100多年后,西方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才进入中国,1300多年后,西班牙探险家哥伦布开往东方的船队才开始启航。